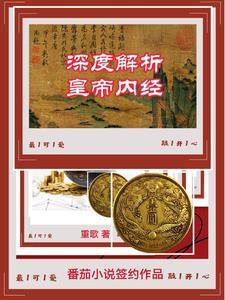7Z小说网>织明 > 第一百一十五章 其所谋究竟有多大(第2页)
第一百一十五章 其所谋究竟有多大(第2页)
其藏,究竟多深?
其所谋者,究竟又有多大?
孙时相在心中暗自揣度,虽然早先便已判断,张诚将来必定会位极人臣,只不过在他的心中,到底是忠,还是奸,一时仍难下判断。
在孙时相心中,大明朝廷、当今皇上、关外建奴、关内流寇,再加上永宁伯张诚,正好是当今天下的五方势力。
现下里看来,崇祯贵为当今大明皇帝,似乎是高高在上,其威仪不可侵犯,然却处处受到朝臣和礼法的掣肘,再加其性格上的缺陷,十余年来非但碌碌无为,更可说是昏招频出。
而朝廷上的煌煌诸公代表着天下士绅一派,他们中虽也分成若干小的派别,但在整体利益的前提下,仍能紧紧抱在一起与当今皇上抗衡,他们是既得利益者集体,相当于当今世上的守旧派。
在此前,孙时相一直认为流寇是一股破坏力量,并不具备建设的能力,他们的出现或许会对各地守旧派官绅势力造成一定打击和破坏,但终究将成为历史尘埃,就如唐末之黄巢一般。
孙时相原本就建奴颇为关注,这或许与他身处宣府,又承袭家学对山川地利颇有研究的原因,尤其是在老奴病亡,新奴酋黄台吉登位之后,建奴那边的诸般变化,更引起了他的无比忧愁。
黄台吉接掌汗位之初,北有蒙古林丹汗,南有朝鲜王国,中间还要与大明边军作战,其形势并不算很乐观,且还略显有些艰难。
可黄台吉励精图治,一改老奴时期对待汉人的杀戮政策,他对内大力提拔汉人做官,笼络民心,对外则先后消灭林丹汗,统一蒙古各部于自己麾下,又征服朝鲜王国,使其成为自己的粮仓。
成功斩掉大明的两条臂膀后,黄台吉的野心才真正暴露出来,他改元称帝,建国号大清,预示着其要与大明一争天下的雄心。
眼看大明朝廷昏聩,内忧外患交困之下,犹如日落西山的垂暮老者一般,一日不如一日,隐隐有亡国之态,建奴屡屡入寇京畿内地,竟无力抵挡。
永宁伯张诚却恰在此时出现在孙时相的眼中,他就如夜幕里的流星一样闪亮,拥强军锐士数万,内剿流寇,外御建奴,且治理地方亦能颇有建树。
张诚的降临,让处于迷茫中的孙时相,仿佛一瞬间看到了新的希望!
正是因为如此,他才主动寻到参将刘广武,向他表达欲为张诚效力的意思,然而如今却也对自己的这一决定产生了怀疑。
他不知道,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否正确,在未来会为自己的家族带来怎样的改变?
…………
四月初九日,晚上,月亮才刚刚升上皇极殿的琉璃觚棱。
崇祯皇帝忽地感到一阵心烦意乱,六神无主的他十分勉强地耐下心来,可又看了一阵文书,忽而长吁了一口气。
只见他起身离开御案,缓步走出乾清宫外,在丹墀上来回徘徊不定。
初夏的夜里仍是十分凉爽,使他发胀的太阳穴有了一点清爽之感,随即又深深地吸了一大口凉气,徐徐将胸中沉郁已久的闷气呼出。
崇祯皇帝暗自数着云板与更鼓声响,不由得更觉焦急起来,在心中暗自问道:“陈新甲怎还未进宫?都已是二更天啦!”
恰在此刻,一个小太监轻轻走来,在丹墀前躬身奏道:“启奏皇爷,陈新甲已在文华殿外恭候召见。”
“啊……辇来!”
原本在今天上午,陈新甲就已经被崇祯皇帝在乾清宫召见过一次,询问他关于中原流贼与关外建奴的应对方略。
陈新甲虽然也算精明强干,然无奈大明这十多年来一直陷入在内外两条战线的困境之下,钱粮枯竭,更兼兵力不足,将不用命,士无斗志,军纪败坏等种种。
如今,要想挽救大明危局已实无良策,所以在上午的召见时虽也密议良久,仍是毫无结果可言。
崇祯皇帝本来就性情急躁,越是苦无救急良策以对之际,他就越发焦急,乃至坐立不安,也更容易在此时爆发出他的坏脾气来。
直吓得在乾清宫里当值伺候的太监、宫女们,个个都是噤若寒蝉,提心吊胆的连个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。
今日,晚膳刚过,崇祯皇帝便得到河南那边奏报,说新任三边总督汪乔年殒命闯贼之手,襄城得而复失,豫省已无兵马可阻挡闯贼大军的消息。
虽然崇祯皇帝本人也不认为,汪乔年之流,会比傅宗龙厉害,也没指望他能够平定豫省流贼,但总该给流贼以制约,使之不能放开手脚攻打开封吧?
怎想到,他才入豫省,便即兵败身死!
所以,河南巡抚高名衡的密奏给他很大震动,几乎使他因辽东大胜奴贼带来对国事之希望,险些因此而全部浇灭……
高名衡在密奏中提到这样一句:“……前有南阳覆灭,总兵虎大威殉国,唐藩蒙难。今陕督乔年身死襄城,豫省已无可战之兵,开封危急,周王危急。
望朝廷速派得力战将,赴援豫省,臣启陛下,急催宣府永宁伯之勇毅军,速速进兵,以解开封之危,救周王无虑……”
崇祯皇帝虽然对外藩各亲王并无多大情感,但开封周王却有些不同。
闯贼大军两度围攻开封,皆未能攻破,虽赖地方文武守土有功,但周王朱恭枵之所为,对于开封固守亦有不灭之功,更不能有失。
况河南乃中原腹地,亦是四冲之要地,若彻底陷于贼手,其西可占陕西,东则侵山东,阻绝运河之南北交通,如此就断了大明京畿的血脉输送啊!
今晚,他因河南流贼之患,又联想到了与建奴“和议”一事,这才急惶惶的命太监传谕兵部尚书陈新甲赶快入宫,在文华殿等候召对。
关于同建奴秘密和议,连崇祯皇帝本人都认为是目前唯一的救急之策,趁着锦州大战之利,他正密谕陈新甲在暗中火速进行,愈快愈好。
“陈新甲毕竟实干之才,与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臣工不同。这满朝文武,或只他一人明白朕的苦衷,肯替朕目前的困境着想啊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