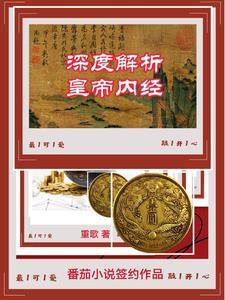7Z小说网>渣攻在强取豪夺文里重生后崔帏之乔云裳 > 第181章(第1页)
第181章(第1页)
郎中给乔云裳看完膝盖,起身,对一脸担心的崔帏之拱手行礼道:
“世子不必焦心。待用金疮药给世子妃涂抹后,一月内必定恢复如初,不会留疤。”
“我不是担心他留疤。”崔帏之道:
“他日后不会留下什么腿疾吧?”
“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”郎中迟疑了一下,随即摇了摇头:
“日后天气冷,或者下雨天,膝盖可能会疼痛,但如果细细保养,入冬后屋内常生炉火,便不会有什么感觉。”
“好。”崔帏之细细记下,片刻后又像是记起了什么,又忙道:
“他腹中的孩子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”
“孩子也没事。”郎中忙道:“若是世子不放心,我再另外开一副安胎药便好。但是世子妃脉象紊乱,气息阻滞,应该是伤心过度的缘故,待世子妃醒之后,怕是要常常劝慰,让世子妃宽心才是。”
崔帏之:“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”
方才还焦急不已的崔帏之此刻却诡异的沉默了,半晌,他才常常地叹了一口气,苦笑道:
“这怕是难。”
他们说话的时候,崔降真就跪趴在床沿边,睁着好奇的圆溜溜的眼珠子,盯着昏迷的乔云裳不眨眼,伸出肉乎乎的小爪子,有一下没一下地拨弄着乔云裳的指尖,像是在好奇为何都白天了,乔云裳他还在睡,甚至现在也依旧不醒。
他想叫乔云裳起来陪他玩。
可乔云裳不知道是怎么了,一觉睡到晚上了也不醒,直到奶妈带他去外头玩儿,他买完风车回来,才看见乔云裳坐在贵妃榻上,双眼失神地看着小几上的肉粥,并不吃,直到崔帏之坐在他身边,拿起肉粥,用勺子搅了搅,随即递到乔云裳唇边,让乔云裳吃一点。
乔云裳把头扭了过去,并没有吃,泪水很快就从眼眶里滚落下来,打湿了他的面庞。
崔帏之没有逼他吃,安安静静地看着乔云裳,片刻后放下粥碗,绕过小几,坐到乔云裳身边,随即伸出手,抱住了他,用掌心轻轻抚摸着他的后脑勺,像是在安慰。
乔云裳的肩膀微微抖动着,片刻后同样同样抱住了崔帏之,隐忍的哭泣声从崔帏之的脖颈处传来,没多久,就变成了悲伤的痛哭。
崔降真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,听的内心难受,于是仰起头,对侍女道:
“绯鸿姐姐,他为什么哭?”
“大娘子是伤心了,才哭的。”
绯鸿蹲下身,摸了摸崔降真圆圆的小脸蛋,随即叹息道:
“大公子,等有一天你长大了,真正经历生离死别的时候,你就会知道,大娘子是为什么哭了。”
可崔降真才不到四岁,他不懂。
他跑到崔帏之身边,抓住崔帏之的指尖,轻轻摇了摇,随即指了指乔云裳的背影,问:
“他什么时候能不哭了?什么时候能陪我玩?我想和小草儿一起去捉蟋蟀,还要和乞娘娘一起吃糯米糕,乞娘娘最疼我了,他还会给我大橘子吃。”
每当说到这个的时候,崔帏之总是以一种莫名的神情看着他,眼神闪动,那神情似乎有些悲伤,但又强装笑意:
“乖真儿,你母亲最近心情不太好,不要在他面前提起乞娘娘,好吗?”
“为什么?”崔降真还不知道姜乞儿已经死了,呆呆地看着崔帏之,疑惑道:
“可我想他带我去找乞娘娘玩。”
乞娘娘人可好了,人又温柔,手还巧,还会给他扎漂亮的双髻。
为什么不能在他面前提起乞娘娘?
崔降真想不通。
他想要乔云裳带他去东宫找姜乞儿和梁雪草,可乔云裳伤了腿,一直没有下床,在床上休养了几天,直到第七天的时候,崔降真一个人花园里逗蚂蚁玩,一回头看见乔云裳沐了浴,净了脸,换上穿着浑身素白的衣裳,头上只戴了两只素玉钗,正在崔帏之和仆役的搀扶下,一瘸一拐地走出房门。
崔降真一个人无聊了好多天,见乔云裳终于可以出门了,赶紧跑过来,抓住乔云裳的手,轻轻晃了晃,随即眼巴巴地看着乔云裳。
乔云裳脸上未曾上妆,素净一片,更显得皮肤如雪一样白。
他低下头,摸了摸崔降真的头发,随即勉强笑道:
“真儿想乞娘娘了吗?”
“想了。”崔降真道:“我们什么时候去东宫找乞娘娘和小草。”
“现在就去。”
崔帏之把崔降真抱起来,避免他冲撞到乔云裳的肚子:
“真儿,待会儿进了东宫,不能笑,知道吗?”
“不能笑?”
崔降真一愣:“为什么?”
“没有为什么。”崔帏之道:“想见乞娘娘,就答应爹爹,进了东宫之后,不能笑。”
“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好吧。”崔降真妥协了:“那我不笑。”
“乖孩子。”崔帏之摸了摸崔降真的脸,随即亲了亲,带着乔云裳和崔降真上了马车。
今天是姜乞儿的头七。
在去东宫的路上,崔帏之和乔云裳都安静的过分,彼此间都没有说话,崔降真是个小孩子,耐不住性子,屁股在坐垫上扭来扭去,片刻后跪趴在窗边,百无聊赖地掀开帘子,向前看去。
只见视线尽头去一片白旗和白幡飘扬,黄色的纸钱撒的漫天都是,天气灰蒙蒙的,远处飞过成群的黑色大雁,发出凄凉的叫声,显地往日华丽巍峨的东宫都如此的灰败起来。